- 本期封面
- 雜志目錄
- 上一頁(yè)
- 下一頁(yè)
- 往日期刊
-
- 主辦
- 中化集團(tuán)辦公室
- 總編輯
- 張寶紅
- 副總編輯
- 郭鳳琳
- 編輯
- 蘇 靜 梁曉亮
- 劉 昕 賈寧遠(yuǎn)
- 設(shè)計(jì)統(tǒng)籌
- 王向東
- 編輯部地址
- 北京市西城區(qū)復(fù)興門(mén)內(nèi)大街28號(hào)凱晨世貿(mào)中心中座1116室
- 電話(huà)
- 010-59568487
- 010-59568098
- 傳真
- 010-59568890
- 郵箱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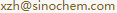
- 發(fā)送對(duì)象
- 公司員工
- 印刷單位
- 京平誠(chéng)乾印刷有限公司
- 印刷日期
- 2020年12月20日
- 印數(shù)
- 10300冊(cè)
- 本刊文章版權(quán)受法律保護(hù),如欲轉(zhuǎn)載,請(qǐng)與《新中化》編輯部聯(lián)系
外派哥倫比亞的1009天文/閆 聰 |
|
一千天很長(zhǎng),讓我對(duì)石油勘探開(kāi)發(fā)行業(yè)有了更深的認(rèn)知和體會(huì);一千天很短,短到來(lái)不及和哥倫比亞的好友一一道別
閆聰 2016年10月,拖著兩個(gè)沉重的行李箱,我獨(dú)自一人來(lái)到位于南美洲的哥倫比亞。站在首都波哥大國(guó)際機(jī)場(chǎng)門(mén)口,望著眼前這片陌生的土地,內(nèi)心激動(dòng)不已。就這樣,我在哥倫比亞的“1009天”外派生活正式拉開(kāi)帷幕。 新的名字 我在哥倫比亞的工作崗位是中化Emerald哥倫比亞公司商務(wù)管理,負(fù)責(zé)跟蹤管理公司的自產(chǎn)原油銷(xiāo)售、輕油及第三方原油采購(gòu)、管道資產(chǎn)的運(yùn)作等事宜。 商務(wù)部的同事是三名年紀(jì)相仿的哥倫比亞女孩,主管Lina非常熱情,一見(jiàn)面就用貼面禮對(duì)我表示歡迎,這讓靦腆的我有些不太適應(yīng),后來(lái)才發(fā)現(xiàn)這是當(dāng)?shù)亓?xí)以為常的打招呼方式。花了整整一周的時(shí)間調(diào)整時(shí)差和適應(yīng)環(huán)境,我也終于記住了她們的名字:Lina Marcela Marin、Angelica Velasquez和Zaida Gutierrez。 第二周一上班,Lina笑嘻嘻地邀請(qǐng)我參加部門(mén)的“迎新聚餐”,“你的中文名字發(fā)音對(duì)我們來(lái)說(shuō)挑戰(zhàn)太大了”,Lina說(shuō),“為了方便交流,我們?nèi)齻€(gè)幫你想了個(gè)西語(yǔ)名字。”恰好那幾天我也一直在琢磨自己的西語(yǔ)名字,“Iván”我倆居然異口同聲地說(shuō)了出來(lái)。這一刻,我突然對(duì)文化的互通性有了新的感悟,不同國(guó)籍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,對(duì)一件事情確實(shí)可以擁有相同的想法。 工作忙碌而充實(shí),轉(zhuǎn)眼萬(wàn)圣節(jié)就要到了。萬(wàn)圣節(jié)對(duì)哥倫比亞人來(lái)說(shuō)是一個(gè)極為重要的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。入鄉(xiāng)隨俗,公司每年都會(huì)舉辦萬(wàn)圣節(jié)派對(duì),大家要準(zhǔn)備節(jié)目在派對(duì)上表演。我們幾個(gè)和財(cái)務(wù)部的同事一起,決定表演電影《Kill Bill》中的經(jīng)典橋段,而我被推選飾演劇中的武林高手白眉,理由是——中國(guó)人都會(huì)武功。 看過(guò)這部電影的人都知道,白眉是一位道骨仙風(fēng)的道長(zhǎng),留著很長(zhǎng)的白胡子和白眉毛。為了達(dá)到更好的表演效果,Lina她們下 了“血本”,跑去采購(gòu)了一米來(lái)長(zhǎng)的白胡子和兩撇白眉作為道具,還不知從哪里弄來(lái)了一身中式白袍。為 了不辜負(fù)大家的期望,我自覺(jué)苦練了一周“陳氏太極拳”,并在活動(dòng)當(dāng)天大顯身手,最終斬獲“最佳表演獎(jiǎng)”,從此成為同事心目中的“功夫小子”。 下山奇遇 波哥大位于太平洋東岸東科迪勒拉山脈的腹地,平均海拔2600米左右,屬于典型的高海拔地區(qū),因此同事們習(xí)慣把去油田現(xiàn)場(chǎng)工作戲稱(chēng)為“下山”。在商務(wù)部輪崗半年多后,我轉(zhuǎn)崗到了計(jì)劃部,并有幸前往位于哥倫比亞南部卡克塔省的Nogal區(qū)塊進(jìn)行現(xiàn)場(chǎng)踏勘。
Nogal區(qū)塊現(xiàn)場(chǎng),在北緯4度勘探找油 前往Nogal區(qū)塊,我們乘坐的是那種只在電影里見(jiàn)過(guò)的最原始的螺旋槳 飛機(jī),由哥倫比亞一家軍民兩用航空公司執(zhí)飛。空姐胡亂比劃完安全提示后,轉(zhuǎn)身推出餐車(chē)準(zhǔn)備為乘客倒飲料,剛走兩步,飛機(jī)就“嗖”的一聲起 飛了。這位空姐踉蹌了幾步,然后滿(mǎn)不在乎地繼續(xù)為乘客服務(wù)。我被眼前這一幕嚇出一身冷汗,但身邊經(jīng)常 飛行的同事卻仍在優(yōu)哉游哉地閉目養(yǎng)神。 飛行了一個(gè)多小時(shí),在經(jīng)歷了無(wú)數(shù)次大小顛簸后,飛機(jī)終于降落在卡克塔省會(huì)弗洛倫西亞(Florencia)。可以毫不夸張地說(shuō),坐落在山谷之中的弗洛倫西亞機(jī)場(chǎng)是我平生見(jiàn)過(guò)的最簡(jiǎn)陋的機(jī)場(chǎng),面積僅有幾個(gè)足球場(chǎng)那么大,且只有一條跑道。 撲面而來(lái)的熱風(fēng)提醒我,已經(jīng)“下山”了。我們幾個(gè)匆忙從行李堆中翻出行李,坐上前來(lái)接應(yīng)的皮卡。中午稍作休整后,我們便來(lái)到位于弗洛倫西亞南部幾十公里外的Nogal區(qū)塊進(jìn)行踏勘。 Nogal區(qū)塊是Emerald哥倫比亞公司在2012年新申請(qǐng)的勘探區(qū)塊,當(dāng)前處于勘探階段,僅完成幾十公里的二維地震采集和一口參數(shù)井的工作量。由于該地區(qū)基礎(chǔ)設(shè)施落后(幾乎沒(méi)有像樣的公路),加之當(dāng)?shù)匕傩蘸偷胤浇M織反對(duì)石油工業(yè),作業(yè)難度極大。本次實(shí)地踏勘的目的,是確定勘探二期60公里二維地震的部署方案,并對(duì)幾條測(cè)線(xiàn)的施工條件進(jìn)行實(shí)地調(diào)研,對(duì)施工周期和費(fèi)用進(jìn)行估算。 彼時(shí)正逢雨季,本就顛簸的鄉(xiāng)村土路更加泥濘不堪。領(lǐng)隊(duì)司機(jī)不時(shí)地探出頭,詢(xún)問(wèn)迎面駛來(lái)的司機(jī)前方的路況。眼看就要到達(dá)預(yù)定的北部測(cè)線(xiàn)位置時(shí),得知前方道路被連日來(lái)的降雨沖毀了,皮卡車(chē)無(wú)法通過(guò)。怎么辦?距離目的地已經(jīng)如此之近,大家都不想輕言放棄,加之被沖毀的路段看著積水并不是很深,于是我們決定冒險(xiǎn)沖一沖。隨著一腳油門(mén)聲,皮卡飛快地沖向積水路段,然而行到正中間時(shí),車(chē)子還是熄了火。 接下來(lái),男女老少齊上陣,從路邊找來(lái)大石塊和粗木棍,撬的撬、推的推、墊的墊,一個(gè)小時(shí)后皮卡車(chē)成功得救。滿(mǎn)身泥點(diǎn)的領(lǐng)隊(duì)司機(jī)招呼大家一起到皮卡前合影,還用蹩腳的英語(yǔ)問(wèn)我“interesting?”我回答,非常有意義,我會(huì)牢牢記住這一段經(jīng)歷的。說(shuō)話(huà)間,我打開(kāi)手機(jī)GPS,這里是北緯4度,應(yīng)該是我在南美洲最靠近赤道的位置。 喜與悲 2017年上半年,妻子來(lái)哥倫比亞探親,臨回國(guó)前驚喜地發(fā)現(xiàn)“兩條杠”的愿望實(shí)現(xiàn)了!在妻子的強(qiáng)烈要求下,我硬著頭皮向領(lǐng)導(dǎo)請(qǐng)了一個(gè)月假,一同回北京辦理醫(yī)院各種預(yù)約手續(xù)。一個(gè)月的時(shí)間轉(zhuǎn)瞬即逝,由于受孕期激素水平影響,妻子變得喜怒無(wú)常。假期臨近結(jié)束,“我過(guò)幾天的返程飛機(jī)。”我小聲和妻子說(shuō)。“不行!”得到的是斬釘截鐵的拒絕。 從戀愛(ài)開(kāi)始,我就知道妻子是一個(gè)“刀子嘴豆腐心”的女孩,她心里縱然萬(wàn)般理解和支持,嘴上卻不愿說(shuō)出“同意”兩個(gè)字。給她做了幾天思想工作,并從老家搬來(lái)母親大人,這才平復(fù)了妻子內(nèi)心的“怨氣”。看著B(niǎo)超圖像上那僅如松子般大小的寶寶,我的眼圈濕潤(rùn)了。 2017年底,我回國(guó)休假。在北京機(jī)場(chǎng)剛剛辦理好入關(guān)手續(xù),打開(kāi)手機(jī)看到妻子發(fā)來(lái)微信“老家出大事了,我在回家的高鐵上,看到速回復(fù)”。惶恐不安的我趕緊給妻子撥通電話(huà),得知岳父出了交通事故。晚上與抵達(dá)老家的妻子和母親聯(lián)系,方得知岳父在交通事故中去世,我趕緊買(mǎi)了第二天一早的車(chē)票,直奔老家…… 短短三年,我經(jīng)歷了女兒出生的大喜,也體會(huì)了親人離去的大悲,變得越來(lái)越成熟。特別感謝家人的堅(jiān)強(qiáng)后盾,讓我能夠堅(jiān)持完成這次難得的海外輪崗,成為生命中一段寶貴的經(jīng)歷。 真正的朋友 2019年7月,我結(jié)束了“1009天”的外派,回到北京總部。一千天很長(zhǎng),讓我對(duì)石油勘探開(kāi)發(fā)行業(yè)有了更深的認(rèn)知和體會(huì);一千天很短,短到來(lái)不及和哥倫比亞的好友一一道別。Emerald商務(wù)部、計(jì)劃部,還有其他部門(mén)的幾個(gè)“鐵哥們”紛紛下載了微信,至今仍和我保持聯(lián)系,我們經(jīng)常互相問(wèn)候,我也不時(shí)分享一些女兒的照片給他們。 2020年,新冠疫情來(lái)襲。我在微信上詢(xún)問(wèn)法律部經(jīng)理Maria Fernanda當(dāng)?shù)氐那闆r,她說(shuō)“We are good, Emerald is prepared, but not the Country”。聽(tīng)到這個(gè)回答,我的心瞬間揪了起來(lái),不由想起Nogal區(qū)塊那騎著馬上學(xué)的小姐妹,想起Campo Rico區(qū)塊周邊那些貧窮而又樸實(shí)的老鄉(xiāng)們,希望他們都平安。 疫情爆發(fā)初期,Emerald哥倫比亞公司的領(lǐng)導(dǎo)同事們四處奔走,為北京總部采購(gòu)口罩,并積極組織捐款捐物;疫情在南美迅速蔓延后,勘探公司組織大家為油田周邊社區(qū)捐款,幫助貧困居民共渡難關(guān)。“真正的朋友,是在困難的時(shí)候幫你一把的人。”對(duì)于勘探公司,對(duì)于Emerald,對(duì)于我們,這確實(shí)并非一句虛話(huà)。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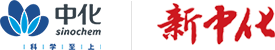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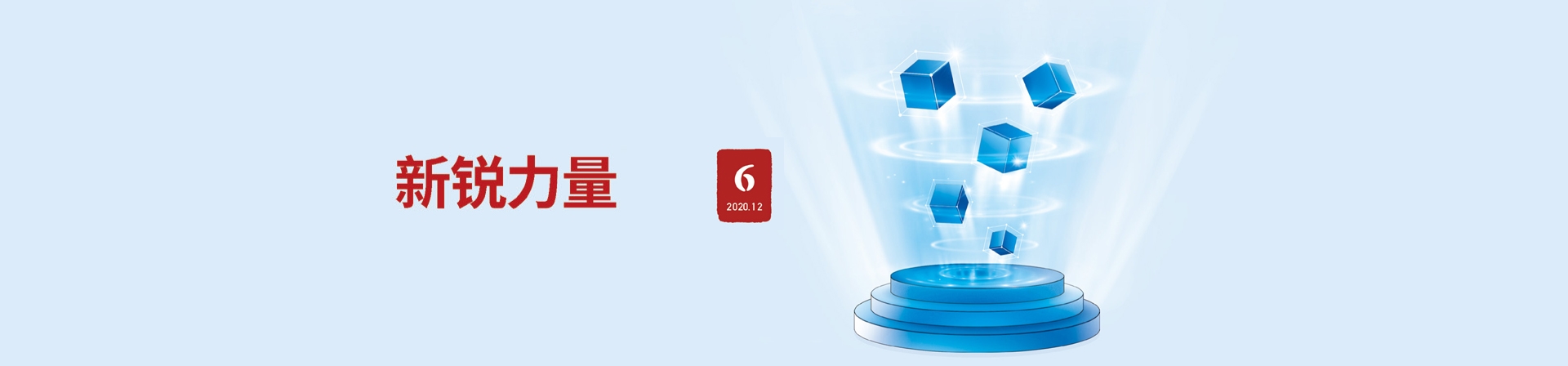



 建議(1024*768) IE7.0以上瀏覽器瀏覽本站
建議(1024*768) IE7.0以上瀏覽器瀏覽本站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