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與中化半生緣文/朱達志 中化公司原副總經(jīng)理 |
|
昔日舊僚相攜過,笑談浮生與流年。今朝回首來時路,眉尖澀澀眼微咸 我今年90歲,不清楚是否走到人生盡頭,但很慶幸,我的思維還夠清晰,記憶還夠牢固,以至于再回首,往事還如一幀幀鮮活的畫面,歷歷在目。從大學(xué)畢業(yè),到鮐背之年,我的前半生都在中化度過。我于中化,如滄海一粟;中化于我,卻是前半生回憶里最重要的存在。 上海往事 1928年1月21日,我出生于武漢。建國以前國內(nèi)形勢動蕩,全家?guī)捉?jīng)輾轉(zhuǎn),直到1940年定居上海。我出生的年代,中國還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。從我記事時起,上海就有租界區(qū)。日本發(fā)動侵略戰(zhàn)爭,上海一步步淪陷。起初日本同歐美諸國維持著表面和平,西方國家租界里依然是“太平盛世”,擁有著上海百姓心向往之的安寧。后來大家的日子都越過越不太平,整個上海淪陷。從抗日戰(zhàn)爭到解放戰(zhàn)爭,直到新中國成立,上海才一步步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安寧,我也才有機會繼續(xù)深造。 回想起來,1940-1945年我一直在上海租界學(xué)校念書。長達十余年的戰(zhàn)爭結(jié)束后,1947年我才有機會到滬江大學(xué)讀書,在企業(yè)管理系學(xué)習(xí)。這是一個美國教會辦的大學(xué),但我不信“上帝”,沒有入基督教,生活比較單純。不是紈绔子弟,也不是埋頭在書堆里的學(xué)生,功課成績過得去,平時看小說、看電影、聽音樂會、打球、打橋牌等,不太關(guān)心政治,對國民黨貪污腐化不滿。通過在大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“新民主主義論”“政治經(jīng)濟學(xué)”“唯物論”等課程,以及閱讀從思想進步同學(xué)那里借來艾思奇的《大眾哲學(xué)》,對共產(chǎn)黨、社會主義有了初步認(rèn)識。那時候,大學(xué)畢業(yè)后統(tǒng)一分配,1951年我被分配到北京,我的人生開始和中化有了交集。 四海為家 第一次離家,心里很忐忑。來京前,我沒離開過上海,沒想到這一上火車,以后的日子就四海為家了。到北京后,火車停在前門站,我拿著行李住在大柵欄糧食店街的一家小客店。五平米的小屋,一個土炕占了一大半,屋頂不高,有一盞灰暗的沒有燈罩的小燈。我坐在屋子里,看著外面來來往往的人群,覺得一切都很新鮮。第二天一早,我到前門附近的貿(mào)易部人事司報到。接待的同志給了我一封介紹信,讓我去天津剛成立不久的中國進出口公司報到。本以為會在北京待一陣子,沒想到兩天不到就去了另一座城市。 當(dāng)時,中國進出口公司辦公地址在天津市遼寧路一座老式洋樓里,幾十名員工來自天津、上海、北京、香港、歐洲、日本和北美,絕對算得上多元化“跨國公司”。報到后,人事處分配我到計劃室工作,科長很有耐心地教我如何做統(tǒng)計報表。那時沒有現(xiàn)代化辦公設(shè)備,做報表主要是靠鉛筆、復(fù)寫紙和算盤。由于進出口報表要分口岸、商品和國別等,剛開始業(yè)務(wù)不熟練,加班是常有的事。政治學(xué)習(xí)任務(wù)也很重,大家都挺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,熱情很高,沒有怨言。我還記得,我的第一份工資是240斤小米(約合人民幣20-30元),開心了半天。 時任公司總經(jīng)理盧緒章,是我黨出色的地下工作者,也是我國對外貿(mào)易工作奠基人之一。中國進出口公司在他帶領(lǐng)下,努力開展“反封鎖、反禁運”斗爭,出色完成了國家賦予的重要使命。 公司在天津開展工作沒多久,就遷到北京。搬遷時,我坐著卡車押運文件柜,來到北京西城區(qū)武定侯一座古色古香的大院里。當(dāng)時心想,這下可算是安頓下來了。沒想到,隨后卻不斷搬家,先是搬到磚塔胡同一座大樓里,不到一年又搬至東交民巷13號,不久我們又把這個房子讓出來給蘇聯(lián)專家用,公司隨即搬遷至新僑飯店。不足一年,我們又遷至臺基廠一處西式大院里。在臺基廠辦公不到一年半,我們遷至西郊二里溝進口大樓。 那時候,大家對于公司這個大家庭的溫暖感受很深。記得剛?cè)肼毑痪玫?953年,公司組織一次體檢,我和幾名同事查出肺部感染。那個年代,肺部感染屬于高傳染、低治愈疾病,公司給我們單獨安排宿舍,單獨安排伙食,還從香港專門進口特效藥,治好了我們的病,我們幾位同事對公司特別感激。雖然四海為家,但公司在哪里,我們的歸屬感就在哪里。我積極向上,努力學(xué)習(xí)、工作,為祖國、為公司誓做一枚永不生銹的螺絲釘,1952年12月加入共青團,195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 “運動不斷” 上世紀(jì)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,“運動”一個接一個,“鎮(zhèn)反”“三反”“五反”“反右派”“反右傾”“大躍進”“文化大革命”等等,這些活動占據(jù)不少工作時間,公司業(yè)務(wù)也受到較大沖擊。好在周恩來總理親自抓外貿(mào),公司總經(jīng)理重視經(jīng)營,我們的業(yè)務(wù)才沒有受到顛覆性打擊。 可能是由于“家庭成分”不好,經(jīng)常要下放勞動。我記得那時候,種過地、除過草、幫過廚、修過水庫、還挖過防空洞。我下放勞動去過陜北綏縣、吉林省舒縣、河南省息安、還有北京小湯山等。 文化大革命期間,經(jīng)常有批斗會、討論會,寫大字報、寫檢查、上街游行等也是常事。文革后期,有次上面通知時任總經(jīng)理趙茂春同志到當(dāng)時協(xié)助周總理抓外貿(mào)的陳云同志那里匯報工作,趙茂春總經(jīng)理要我陪同前往。匯報后,陳云同志對我司天然膠業(yè)務(wù)很關(guān)注,這對公司的進出口業(yè)務(wù)起到促進作用。 空中飛人 1978年,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。鄧小平同志吹響改革開放、振興經(jīng)濟的號角。公司也因國內(nèi)經(jīng)濟形勢回暖走向高速發(fā)展期,進出口規(guī)模不斷增長,公司貿(mào)易額突破100億美元。1988年,經(jīng)國務(wù)院批準(zhǔn),中化成為國際化經(jīng)營綜合試點企業(yè)。1989年,美國《財富》雜志登載中化公司進入世界500強榜單。從那年起,中化集團先后28次入圍世界500強。 我很幸運,趕上改革開放、國際化經(jīng)營的浪潮。1978年到1986年,我先后五六次擔(dān)任廣州出口交易會化工貿(mào)易團團長,帶隊出訪歐洲、美洲、亞洲十幾個國家和地區(qū),在香港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漢堡主辦過展銷會、洽談會。1982年我被公司提拔為計劃處處長,1983年4月,被任命為中化總公司副總經(jīng)理,1985年到1986年我還兼任公司黨委書記。 1986年10月,公司派我到中化美任董事長兼總經(jīng)理。抵美后,中化美在總公司大力支持下,業(yè)務(wù)發(fā)展很快,并先后成立舊金山、洛杉磯、休斯頓公司,由我兼任董事長。1988年11月,中化美集團公司成立。總公司并購美國太平洋煉油公司半個煉廠后,中化美公司根據(jù)總公司指示,要在美國購置一個磷肥廠。我們把消息放出后,有兩家有意賣給我們,于是我們聘請會計師事務(wù)所和律師事務(wù)所,進行調(diào)查、評估。經(jīng)過一段時間的調(diào)研、談判,最終在總公司授權(quán)下,購置美國原鋼鐵公司所屬的美國農(nóng)化公司,1989年2月9日簽訂合同。該廠年產(chǎn)磷肥100萬噸,450個員工,我們決定工廠名稱不變,仍叫美國農(nóng)化公司,我兼任第一屆董事長。1989年3月8日在工廠召開第一次董事會,我在會上向員工宣講中化精神“開拓、求實、高效”。 坦白說,在美國開展各項業(yè)務(wù)不能算一帆風(fēng)順。人生地不熟,陌生的文化、陌生的任務(wù)、陌生的語言,我在各地兼任董事長需要開會,并購工廠要調(diào)研談判,有時候早上還在紐約,下午就到了洛杉磯或休斯頓,很忙碌。按美國法律,公司在紐約,但出差在外時間長可以減稅。我統(tǒng)計了一下,1992年我出差在外143天。 回想起那段日子,剛開始是假裝堅強,后來就真的堅強了。中化美的同事很團結(jié),也很有凝聚力。大家覺得,只要我們能相聚在一起,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,碰到困難我們一同承擔(dān),困難就不復(fù)存在。我們相伴相助,不論什么苦澀艱辛的事,都能變得甜潤。1993年初我65歲,調(diào)回北京,在總公司做了三年左右顧問。 逝者如斯,行至暮年;紅陽西垂,靜坐庭前。四季流轉(zhuǎn),仰望蒼天;今夕百年,似一瞬間。昔日舊僚相攜過,笑談浮生與流年;今朝回首來時路,眉尖澀澀眼微咸。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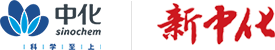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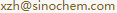


 建議(1024*768) IE7.0以上瀏覽器瀏覽本站
建議(1024*768) IE7.0以上瀏覽器瀏覽本站




